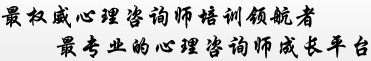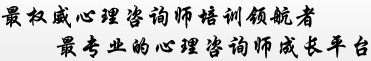寻找文革隐伤者
如同控制录影机,顺放或倒带,一名心理治疗师正在让一名中年男性回溯自己的一生,寻找那个影响他最深、最重大的事件。治疗师称其为“节点”。
记忆的门逐渐打开。这名男子首先想到自己10岁时,被父亲用皮带痛打的情景。描述这一记忆时,他全身抖动,流下眼泪。
当治疗师问,是否还有其他画面可以回放?男子将想象退回到5岁,突然,他出现了姿势的改变,声音变得极为幼稚,失控地用手捂住眼睛,不连贯地喊着“怕、怕”的字眼。当问他眼前是什么,他说看到“文革”时,红卫兵冲进他的家,将一向是权威的父亲拉到院子里,勒令其跪下,用铜头皮带死命抽打的场景……
上述案例,是心理学家[施琪嘉]在2010年众多访谈中的普通一例。十余年来,这位武汉市心理卫生研究所的所长,一直致力于解答这样的问题:已结束近四十年的“文革”仍如何隐形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内心与生活?
他的工作可以用孤独来形容:一直处于地下状态,难以发表论文,也极少公开讨论,研究者更是寥寥可数,“十个手指头就可以数过来”。
这群中国研究者得到的唯一支持,来自德国。自1980年代后期德国学者将精神分析理论引入中国临床心理治疗后,出于由“柏林墙”记忆中艰难痊愈的同理之心,研究一直得到这群异乡人的帮助。
中德两国学者尝试着将精神分析理论引入对“文革”的观察,持续近二十年的研究发现:“文革”的心理创伤不仅持续地影响着亲历者,还对其子女乃至后世数代人产生了代际传递。
尤其值得重视也长久被忽视的是年轻一代的问题——他们承担了父母在“文革”中未加处理的创伤,被父辈施加的精神重担无声改变着。
这种影响后代精神活动的心理机制,被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主席主席阿夫·葛拉赫(Alf Gerlach)称为“跨代际授权”,最明显的后果是损伤后代的思考及记忆能力,“孩子陷在父辈的经历中,重复着其经历的创伤。”
这也是[施琪嘉]及其同伴一直试图治愈的伤痕,“‘文革’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创伤,它至今仍在生疼、化脓。这段记忆需要获得治疗性的处理。”

弗洛伊德:从“柏林墙”到“文革”
心理咨询师陆晓娅从未想到,于她而言,“文革”从未远去。
伤痛的再度来临是在2007年,这位出生于1952年的老人参加了一个由香港治疗师组织的心理工作坊。这是她作为心理咨询师的一次例行培训,工作坊上,每个人都需要说出自己的故事,以完成自我体验。
无意中,有人提到“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父亲自杀对自己的困扰。出乎意料地,悲伤和愤怒一瞬间在房间里弥漫,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
培训者大都与陆晓娅同龄,均是“文革”的亲历者。香港的老师感到吃惊,他很难理解这群老人到底经历了什么。他决定邀请所有人说出自己的故事。
站出来的都是受害者:目睹自杀、被抄家、作为“狗崽子”受尽羞辱……经历了一夜的失眠与胃痛后,陆晓娅也说出内心的痛苦:“文革”中,她曾用军用皮带,抽打过自己的老师……
曾经一度,陆晓娅将这段记忆封存,很少再回忆;作为《中国青年报》为青少年提供心理咨询帮助的“青春热线”的创办者,她也自认为完成了心理上的治疗与痊愈。
残酷的回忆却如此轻易的方式刺入心头,这让陆晓娅意识到:“文革”是一件“未完成的事”,表面愈合的心灵伤口,其实一直在化脓。
陆晓娅尝试做更理性的思考:她开始观察自己,乃至经历过众多政治运动的母亲,借此分析“文革”创伤所带来情绪与行为问题:反应过激、焦虑抑郁、缺乏人际信任……
远在千里之外的武汉,[施琪嘉]也早在进行类似研究。自1996年由神经内科医生转向心理治疗后,施琪嘉一直尝试着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文革”心理创伤及其代际传递。
神经科学的理论基础帮助了他,大量研究后他发现:创伤记忆,带着强烈的负性情感片断,会储留、堵滞在杏仁核内(右侧脑岛),不能正常上传到负责记忆整合的海马,并进一步处理到皮质,因此,它会如一个深藏在体内的发炎脓肿一样,不断地影响着机体。
“这是大多数‘文革’亲历者未曾意识却始终承担着的梦魇。” [施琪嘉]说,“痛苦的回忆会反复以各种形式——画面、声音、味道、皮肤感觉的闪回,一直存在于受害者的头脑中。”
[施琪嘉]的研究,受益于他的老师——德国精神分析学家安姬·哈格(Antje Haag)。
1988年,安姬·哈格首次前往中国授课。她发现自己的“学员”里,一部分年纪较大,都是50岁上下的男性,是在“文革”中被禁止从业的精神病科医生;另一部分年轻学员,则都不满30岁。
明显的年龄层空白——“文革”时许多大学都被迫关闭。学员们随后表现出的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强烈兴趣,更让这名德国人深感触动。
这群学员急切地想要学以致用,治愈时代的病患--1982年,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主席玛格丽特·哈斯·维瑟加尔特(Margarete Hus Wiesegart)参观在北京、成都及上海的精神病院后发现:住院患者多被诊断为重性精神病,其妄想和幻觉都来自政治运动的影响。
1996年,原《工人日报》记者吴琰也曾以“世纪之患”为题采访北京多家精神病院。她发现医院里大量的精神病患者仍沉浸在红色岁月,一些患者甚至出现了病理性象征性思维:会彻夜抱着暖气管睡觉,因为构成暖气管的钢铁代表着“工人阶级。”
1997年,“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正式运作,在德方的帮助下,精神分析理论也被引入对“文革”心理创伤的研究中。
1999年,曾在德国做过辛提人和罗姆人(纳粹时期欧洲被害族群)创伤研究的安姬·哈格,联合6位中国学员,开始了对于“文革”心理创伤的研究。
“德国关于二战及”柏林墙“时期的幸存者及其后代的大量研究,让我们有一定经验对于‘文革’时期的这段历史进行类似观察。” 安姬·哈格说。

“躯体化”与记忆病毒
心理分析学家托马斯·普伦克斯始终记得时年73岁的老王。
老王向他形容打开记忆闸门的艰难,“除了痛,什么也没有”。往常,他从不主动想起任何过往的情节。记忆却常会自动惊醒他。
天下雪了,他会记起自己被流放的那日,当他到达院子,全身白得像雪人,只感到极度的冷。
如果是深夜,他则会想起另一个熟睡的晚上。人们冲进屋,把他从床上拉下,用皮带整晚抽打。因为流血,衬衫粘在伤口里,随后被撕掉,有人从厨房里拿盐往伤口里撒。他甚至还能清楚回放人们如何在他孩子的大米粥里撒尿的画面。
日常生活的感官刺激,都会让老王重回过往,直接通向时间另一边的现场。
“我们把这些创伤症状称作‘闪回’。”托马斯解释说,“都像定时炸弹般被埋藏起来,旁人可能根本看不出来,引爆却会瞬间发生”。
随着访谈的深入,研究者感到愈发震惊,他们将接触到的内容形容为“极度的创伤”。
创伤中首先充斥着的是各种暴力的细节:连夜审讯,剥夺睡眠,公开的羞辱,用皮带拷打,强迫脱光衣服,甚至强制性自杀……
访谈现场,这些受访人常会不由自主地落泪、抽搐,甚至昏厥、口吐白沫。回忆往事,就像“被故意揭开无法愈合的伤口”,他们会感到抑郁和愤怒的交织,伴随出现若干生理反应:失眠,焦虑,暴躁,强迫症,乃至剧烈的呕吐、头疼。
1980年,美国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曾在湖南选择了一百个被诊断患有神经衰弱的病人进行访谈。他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曾在“文革”中遭受影响,比如家庭破碎、失业、子女离散等。有些患者则出现了各种身体上的疼痛,如偏头痛、胃痛、心血管问题……
凯博文将这种身体性的疼痛,称之为“躯体化”——当个体的苦痛无处排解,只能通过生理疾病的方式表达,“躯体化成了这一代人生活苦难的首要表达方式”。
躯体化之外,托马斯还发现老人们持续数十年与往事作战,无休止的羞愧、焦虑、紧张,以及源自生理摧残的恐惧,让他们选择了删除一部分记忆。
托马斯的受访者中,大多将自己描绘成受害者。仅有一位受访者描述了自己作为加害者的行为——她在人事档案中搜寻成分不纯的“可疑分子”,并咒骂他们。
“要承认自己曾是迫害者,意味着承担愧疚。大多数人很难做到如此。他们更习惯选择用否认和放弃来躲避这些感受。”托马斯分析。
“这些创伤,都像是被植入的电脑病毒,潜伏在系统中,伺机而动,也可能随时感染其他的电脑。” 托马斯这样形容创伤性记忆的特点,“没人能说清何时会瞬间崩盘。”

隔代感染者
“伤痛是一笔遗产。”数十年研究,让阿夫·葛拉赫教授有了自己的结论:集体创伤的影响绝不只作用于亲历者,还会对其子女乃至后世数代人产生代际传递。
“幸存者的孩子生活在两个现实中,一个是自己的现实,另一个是由父母的创伤史构成的现实。”
E是阿夫·葛拉赫的一名德国病人。
他的父亲曾为纳粹组织服务,并为德国对抗苏联的战争感到激动;而他的母亲曾是纳粹分子--这些记忆的遗产,令E的羞愧和绝望无处释放。
父辈的伤痛与耻辱让E感到自己从出生就被“惨痛地遗弃”,他把自己塑造成最绝望的人,狂躁而愤怒。
这让阿夫·葛拉赫想起另一个中国病人。1990年代末期,这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德国写博士论文。到达德国后,他陷入长久的孤独和绝望。这让阿夫·葛拉赫困惑——这位30岁的年轻人,在中国颇受重视,和妻儿恩爱,把各种关系打理得井井有条,“怎么会如此绝望?”
后来,阿夫·葛拉赫发现:当他和家族分离,隐藏的父辈记忆才被激活了。“文革”期间,他的祖父被公开羞辱和批斗,祖母则被下放到离家两千公里外的农村劳动改造。
接受心理治疗期间,这个年轻人缓慢而低声地哀悼、抽泣,讲述时断时续。随后的访谈显示:他的生活显现出一种典型的防御本能及处理机制——他只能不断努力工作,才能遮蔽和克服父母和祖父母被迫害的痛苦。
父辈把精神重担传递到后辈——这种影响孩子精神活动的心理机制被阿夫·葛拉赫简称为“代际授权”,最明显的创伤性后果便是损伤后代的思考及记忆能力。
“无论是德国或中国,这些案例共同的特点都是孩子陷在父辈的经历中,复制其经历的创伤,无法形成真正的自我认同。”阿夫·葛拉赫说。
阿夫·葛拉赫的理论,得到了大多数中国同行的认可。这源于他们在大量访谈中的观察。
首先被传递的是暴力:
出生于1971年的易女士,从小接受父亲严格的教育,她逐渐认同了怀揣坚定信仰、暴躁、攻击性极强的父亲。这直接导致了成年后的她,像昔日的父亲一样,殴打了年幼的女儿。
在托马斯的研究中,绝大多数的受访者将自己的父母描述为“专横、严格、充满仇恨”,教育的恶果则会在多年后凸显而出:少年们仇恨并背叛自己的父辈,随着时间的推移,“弑父者”却变得越来越像他的父母。暴力在悄然间传递。
随后被摧毁的,是年轻人们对家庭的看法。
出生于1968年的王先生,懂事后就发觉父母的婚姻是一场政治刑罚——为警方工作的父亲,在“文革”中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并被强迫与一名派去的女人结婚,她属于贫农阶级,人们认为他应该“向她学习”。
王先生在极端压抑与充满争吵的家庭中长大,他将父母的管教称为“‘文革’式的教育”:消除思想,强制服从,并且“经常被打”。
痛苦的经历,让这个男子对家庭失去了信心,成年后的他决定永不结婚,“家庭被政治主宰,这个家有什么好处呢?”
施琪嘉的学生、中国地质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生林瑶,则在访谈中遇到了一个让她意外的对象。
这个年近40岁的中年男子,将自己一生性格的悲剧归咎于被“文革”摧毁的童年:年幼的他,曾目睹许多人闯进家里,夺走了所有东西;原本是富家小姐的母亲,也在这场变故中变得易怒、压抑、嗜用暴力。
此后的数十年,这个男子逐渐感到自己身上缓慢而巨大的改变:他变得木讷、谨慎、敏感,更为重要的,他在潜意识中认为:有钱,就有灾难来临。
这种无法说明的恐惧笼罩着他,以至于他特别“害怕成功”,总会将一些事情刻意弄得糟糕,比如升迁,比如婚姻。
“我的整个人生都被毁了。”回忆这一切,男子声泪俱下,声音变得尖利。目睹家庭的巨变,他无法理解,也从未得到解释。林瑶突然明白了这样一点:“文革”的下一代,是更加负重累累的一代。
⊙版权声明:文章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深圳市心理行业协会心理咨询师技能成长专业委员会由翟文洪老师领队,富有经验的专业人士组成,为您提供专业的技能提升平台,工作宗旨让更多的获得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认证后的合法咨询师掌握咨询设置、初诊接待、初次访谈等实际咨询中的重要环节。遵循职业伦理,协助他们较好的把控咨询初期训练与学习的方向及路径。
致力于高品质的心理学学习,
更多精彩信息即将到来。
最新心理咨询师培训相关咨询,详情请电:
0755-25982119 翟老师
微信:634071804
0755-82412308 古老师